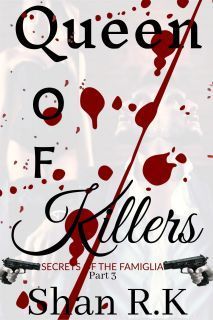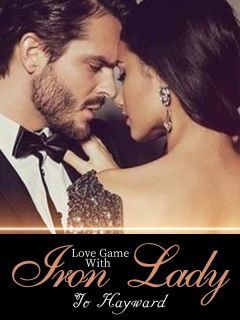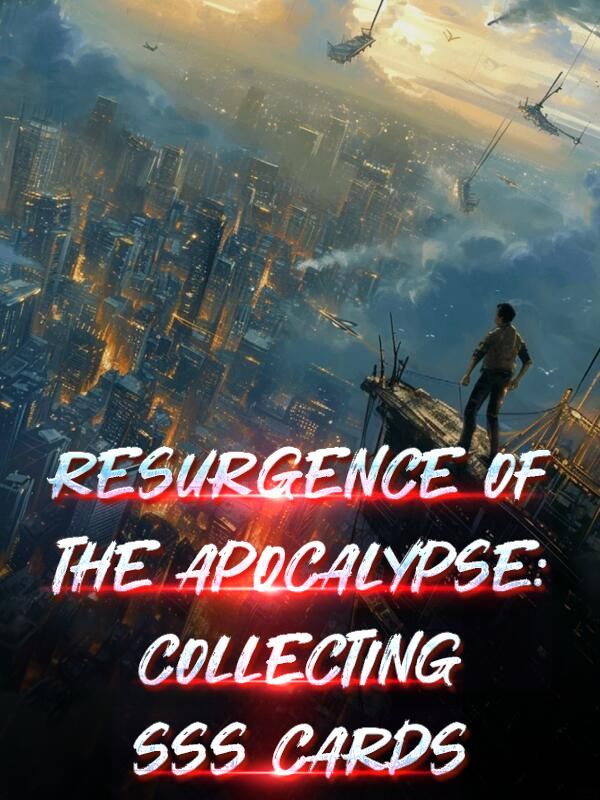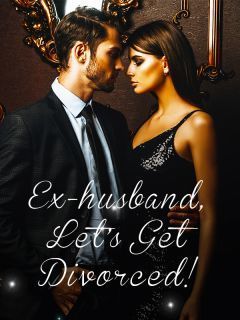艾莉亞娜·卡佩羅·卡泰利
現在
通往天堂的道路始於地獄
但丁·阿利吉埃里
「薩爾瓦多,我需要你。薩爾瓦多,」我衝著空蕩蕩的教堂尖叫。我的高跟鞋在地板上咔噠作響,我的呼吸聲聽起來很刺耳,因為我瘋了。我的腦海裡一片混亂,我衝下了走道。
「薩爾瓦多,我知道你在這裡,」我喊道。他高大的身影從後門走了出來。他穿著黑色褲子和一件黑色襯衫,戴著牧師的衣領,這強烈地提醒了我發生的所有事情。我手指上的戒指在我手裡沉重地壓著,我面對著這位多年來一直為我服務的男人,卻不知道他選擇保護的惡魔。當他站在我面前時,他臉上的疤痕格外顯眼,他的手指緊緊地交織在一起。
「已經快一年了,艾莉亞娜。你做了什麼?」
我跪倒在地,「是,我沒有做。原諒我,神父,因為我犯了罪,」我說,我的身體釋放了多年來一直壓在它身上的緊張感。
「哦,艾莉亞娜,你做了什麼?」我抬頭看著聖安東尼教堂的神父,他曾經是我的忠誠的士兵,並贏得了他的自由。
當我像多年以前一樣,凝視著他嚴厲、毫不妥協的目光時,一顆淚珠出賣了我。只有在那時,我才是一個被我父親的毒藥和國王的殘酷所觸及的女孩。現在我是一個女王,穿著地獄的長袍,浸泡在無辜者的鮮血中,並被一個毒液之王擁有。我跌入了地獄的深淵嗎?
「艾莉亞娜,告訴我。」薩爾瓦多不知道當他說出這些話時,他在尋求什麼。但我抬頭看著這位天真的神父。
「我殺了他們所有人。」
人生的某個時刻,即使是被詛咒的人也必須承認真相。有那麼一刻,我們擺脫了一切。那一刻,你站在那裡,一切都朝著你襲來。所有謊言,你編造的故事,你傷害的人。那些你背叛和毀掉的人,完全沒有任何正當的理由,除了希望這樣做可以減輕你心中的痛苦,也許明天會是一個更美好的日子。但事實並非如此。我活過,愛過,感受了他們教我不要去感受的每種情感。
在我29年的人生中,我做了任何正常人都無法想像的事情。我的故事不是一個關於對一個男人的愛的故事,而是關於對許多男人的愛的故事。對一個總是希望我最好的父親的愛,即使他表現出來的方式是錯誤的。
我愛他的一切。無論是他深邃的靈魂中殘存的善良,還是他對權力的渴望,導致許多人進入了來世的大門。我對他的愛是……是永恆的,即使他是帶領我走向誘惑的蛇。
然後是我對在芝加哥和我一起長大的4個男孩的愛。我從未想過的兄弟,直到他們向我展示了屬於某個事物的感覺,而這不取決於我血管裡的血,也不取決於塑造我的性別。羅密歐、麥可、加百列和羅倫佐是兄弟,他們成了我的一部分,直到其中一個倒下,其中一個背叛了我們。
最後,我對兩個男人的愛,他們都屬於暗影。一個決心成為所有中最有權勢的惡棍,另一個——只希望和我在一起。但嫉妒、仇恨、報復和榮譽扭曲了所有美好,我的故事變成了一個苦澀的故事,愛上你的敵人並遵守對我發誓要保護的人的承諾。我的故事既不是悲劇,也不是幸福的結局,但它是我自己的,我還活著,所以我終於可以講述它了。
「薩爾瓦多,我必須坦白。」我跪著,他的手指解開了,他粗糙的手指抓住了我的下巴。我抬起頭。
「我會聽的。你答應誠實地坦白,只說真話嗎?」他問了多年前問我的問題。只有在那時,我才離開了他,為所有我傷害的人感到羞愧。現在,我不再被過去的決定所困擾,我準備好贖罪了。
「是的,我會告訴你一切。我的坦白始於13年前,當我們達成協議接管芝加哥時,伊麗莎·羅索將成為我們的誘餌。」
「那時候有什麼不好的嗎?」
我望著薩爾瓦多,他穿著牧師服,一位幾乎從上帝的扶手椅上跌落的聖人。
我笑了,但那不是幸福,而是羞愧、尷尬和內疚。
「我撒謊了。」
-----
第一部分
過去、痛苦和感知
艾莉亞娜
13年前
過去永遠不應該存在於現在
而現在永遠不應該給未來蒙上陰影。
謊言,蓄意欺騙的虛假陳述,故意的謊言,謊言。
「你們到底在搞什麼鬼?」加百列問道,他坐在梅羅身旁的鋪著地毯的地板上。回到西雅圖感覺棒極了。再過不久,我就能說出我終於要把芝加哥拋在腦後了。
芝加哥是我會形容為監獄的地方,專為我們五個人而建。我們本來打算明天一早就包機。但我無法再忍受一個晚上,一個城市被像對待老鼠一樣對待。包圍我們的不是成年人,而是有一天會控制它的青少年。我知道不要告訴我的父親,加百列、梅羅、麥可和倫也知道,當卡波·斯塔吉奧·羅索說青少年問題就是青少年問題時。他的話不僅僅是話語,而是對在他的領土內發生的事情保持沉默的警告。
那是暑假,爸爸明天才會從他去東非的旅行回來。這讓我們提前到達,正是放鬆過去幾個月來一直壓抑的緊張情緒的最佳時機。現在發生了很多事情,加百列和倫都想為羅索的血做點事情。他們是芝加哥頂級的犯罪家族,也是我們的主要監護人,直到我們高中畢業。
在第五州,一群男孩被送到他們盟友的領土是一種規則。這意味著一種善意的姿態。但我父親給我派了一個女孩到芝加哥,我們的Famiglia。卡泰利一家堅持我們給予他們同樣的尊重,所以羅索一家派來了伊麗莎。她本來應該是他們的貢品,但結果她是我的父親的女兒。說到糟糕的家庭。而我的就在最上面。
不僅僅是伊麗莎,她戴著非婚生女兒的頭銜,還有另一個不太好的女孩名叫艾麗斯。她已經是成年人了,是馬特奧·迪薩爾沃的姐姐,馬特奧·迪薩爾沃是羅索家族中一個非常令人討厭的成員。或者如果我誠實地說,我應該換句話說,我最討厭馬特奧·迪薩爾沃。其他人從未真正不喜歡他,他們只是討厭他所代表的。我討厭他。
「你去哪裡匆匆忙忙地跑掉了?是去給你的叔叔當好孩子,還是你決定繞道去某個紅頭髮的家?」麥可問加百列。麥可在我白色的棉被下面很舒服,玩著他從機場買的彈簧刀。倫和我佔據了床的左上方,瀏覽著散佈在我半張床上的數百張照片。
我們正在像往常一樣決定哪張照片最適合向我們的父母展示。為了不挑起戰爭,我們試圖保持快樂孩子的樣子。也為了不要看起來像冰做的一樣。我父親說,一個被製造出來的人不需要在火中行走時燃燒。我不確定一個人如何在火中不燃燒,而火是要燃燒的。
我們已經多次在火中被燒焦。唯一的區別是我們的傷疤在裡面,而我們的眼睛的窗戶太小,無法注意到。
實際上,我們已經習慣了亞歷克和他的團隊想方設法擺脫我們的欺凌、陰謀和計劃。但是打斷加百列的汽車剎車就創下了紀錄。他們玩危險的遊戲,雖然我們大多數時候都比他們更聰明,但我們知道我們的時鐘在滴答作響。
「你認為我們能把這個爛攤子維持多久?」倫問我們,舉起一張我們五個人在比薩店的照片。
「我說我們站起來,明年我們就離開那個爛攤子。這將是給羅索一家上一課的完美時機,」加百列在地板上說道。他藍色的眼睛擴大了,注視著倫,當我感覺到他對復仇的期待和渴望在整個房間裡迴盪。
「我沒看到亞歷克統治芝加哥,他會引發一場全面戰爭,卡波·代·卡皮最終將不得不介入。卡西奧和卡梅利德是嘍囉,都不是叫囂著卡波,我懷疑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有足夠的大腦容量來正確刷牙,更不用說統治像芝加哥這麼大的城市了。然而,馬特奧……」梅羅表達了我們都在想的事情。羅索家的兩個男孩都不適合處理像芝加哥這麼大而危險的城市。
「馬特奧將成為迪薩爾沃的卡波,他的家人與英格蘭的莫雷蒂一家關係密切,迪薩爾沃一家一直與加洛家族一起管理洛杉磯。我懷疑他是否想統治一個到處都是羅索人的地方。芝加哥對他來說什麼都不是,只是他父親把他扔下的土地,」麥可說道,從地上站起來,伸展他精瘦的身體。他在青少年晚期變得更強壯了。我能看到他充滿運動感的腿的承諾,透過他穿的深色水洗牛仔褲,好像它們是為適合他身體的每個部位而製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