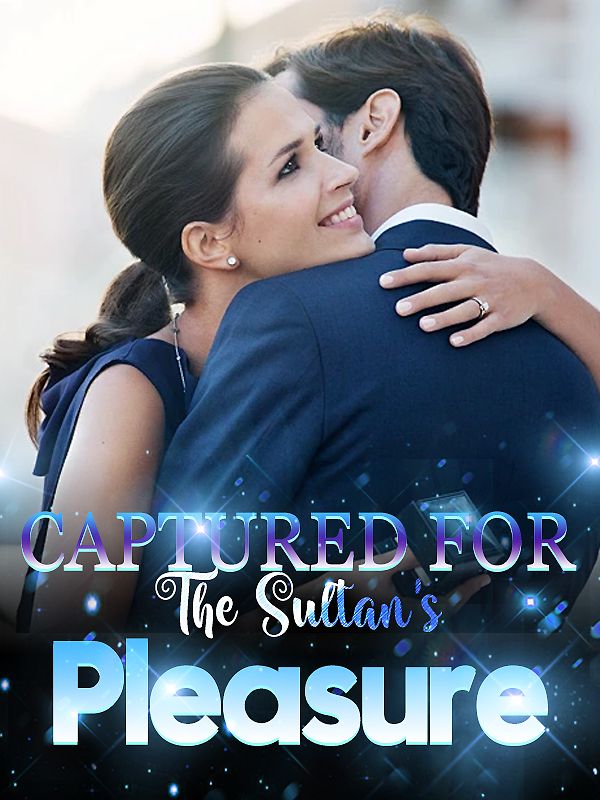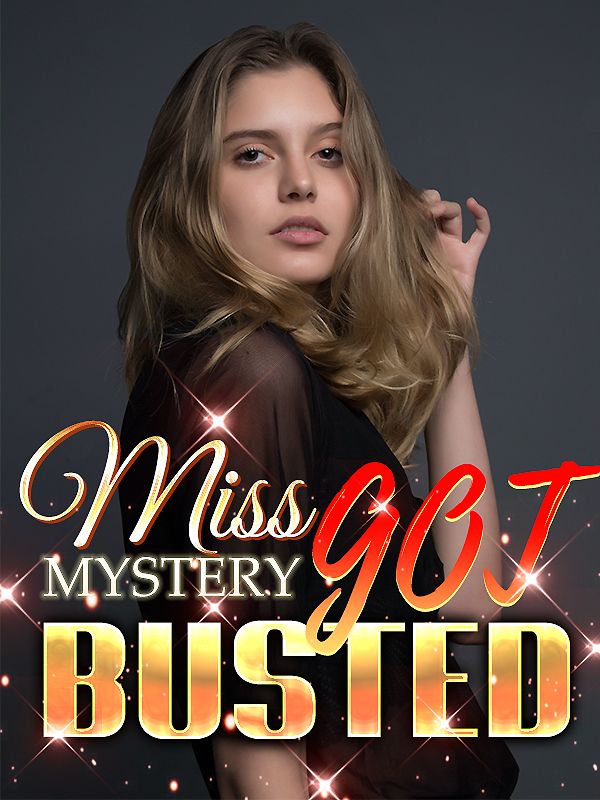玛丽莎气得都要冒烟了。今天本来开局挺好的,结果成了她这辈子最倒霉的一天。
她等了太久了。太久了,都想把自己给洗白。她甚至希望给自己起个新名字。一个能抹掉她过去所有污点的名字。
今天给了她一个完美的机会,让她可以重新融入上流社会。结果,经过早上发生的事情,除非有奇迹出现,否则她就完了。
所以,没错,她生气了。
四年来的辛苦全都白费了,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更恨自己,还是更恨那个惹事儿的人。
为什么他总要这么难为人呢?要是当时他不在,换成别人就好了。玛丽莎肯定觉得,情况不会变得这么糟糕,不会像现在这样完蛋。
为什么他总能从折磨她身上获得乐趣呢?她想不明白,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都是他的错。她终于下了决心。
“啊!” 她尖叫着,一把拽着头发,烦躁地要死。
“谁没事儿一大清早出去骑马啊,真是的!”她自言自语,边走在一条空无一人的柏油马路旁的小路上。
今天天气真好,风景也不错。换了任何一天,她都会花时间欣赏风景。沉浸在大自然的美景中,但现在同样的风景却像是在嘲笑她。这让她心里翻涌出一种感觉,让她本来就糟糕的心情雪上加霜。
然而,白杨树依然在风中摇曳。棕榈树高耸地伫立着,对着上午的阳光挥舞着它们的枝条。远处的地平线上,一座伟大的城市的轮廓在闪烁。高耸的,闪闪发光的玻璃摩天大楼浸没在一片绿色之中。
那原本是她今天的目的地。
她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但她的行为并不能抹灭这一切的美丽。不是城市的美丽,也不是它西边几里地外闪烁的蓝色湖泊。
那是尤尔布湖。这座城市的瑰宝,维特鲁姆的首府。她本来应该去那里的分院,但多亏了他,还有他无休止的恶作剧,结果她没能赶上去参加她的新工作面试。
她的思绪飘回了那件事,玛丽莎发现自己皱着眉头,回忆着她脑海里的画面。
“她们是谁?” 她自言自语,回忆起那些围着他,还有她另一个死对头吉纳维芙·马瑟斯的女士们。
“他的访客?还是他后宫里的人?” 她刻薄地补充道。她还记得那个人对她说过的话有多么残忍,这让她很生气。
“勾引他?真是荒谬的想法!”她嘲讽道。愤怒和怒火中烧,这很快变成了一种受欢迎的干扰,很好地服务了她的逃避主义。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她。玛丽莎是个无法忍受承担责任,或承担她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的人。
这比思考另一种选择,或者很快将在维特鲁姆的葡萄藤上传播的流言蜚语要容易。这更容易。她决定走上愤怒的道路。
“勾引他?” 她对自己重复着这些话。她思考着它们,只是为了不让自己的思绪朝那个方向发展。
“好像我会屈尊降贵到那种地步。他觉得一个人可以变得多么绝望?”尽管如此,她的原则仍然对她很重要,而且她发现他会这样想她,这让她怒火中烧。
不仅被他的话语袭击,也被那天早上的画面冲击着,玛丽莎摇了摇头,但这些想法却无法从她的脑海中抹去。
这很痛苦,而且这些想法越是挥之不去,她就越是烦躁地呻吟着。她挣扎着不去抓自己的头发,而她的挫败感从她所有的精神入侵中清晰可见。然而,她还是忍不住想:“我现在该怎么办?有没有办法挽救一个已经无法挽回的局面?”她思索着,同时低头看着自己那只沾满泥巴的鞋子,这与她现在所走过的干净的灰色沥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根本没有别的办法了。她终于认输了。无法避免后果,而这一次,这将是一场史诗般的丑闻,即使不像四年前那么大。
“为什么我不能把该死的围巾放一边呢?”她诅咒着,穿着她那只红色的脚撞在了另一块石头上。那块小石头松动了,散落到了她面前的大马路上。
“还有该死的风!”她刻薄地说道,拖着一只赤裸的脚和一只带断了的鞋跟的红色鞋子走在狭窄的柏油小路上。
她现在的样子本身就证明了她的磨难,考虑到她那天早上有多么好心情。这也解释了她每走一步,就有多少松散的石头不断地飞出去。
她很幸运,这条路也很空。通常都是这样,但是由于她早上发生了不幸的事情,她也怀疑大自然本身串通一气,要让她出丑。
“大自然在密谋对付你?” 一个声音嘲讽道。
她能听到其中的笑声,而且更多的是,她最不希望听到的舌头所包裹着的恶作剧。
“现在不行……”她在心里呻吟道。“我的日子已经够难过的了,不需要再加入这种疯狂了。”她自言自语道。
“或者说,是真的有个人在说话?” 她打起精神,向四周望了望,并大胆地希望。
“是我,笨蛋!”那个声音补充道,玛丽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这么倒霉。“你从来抓不住重点,真是太神奇了。把自己弄成这么傻的样子,这有什么意义呢?”那个声音唠叨着,她可怜的心再也承受不住了。
惊喜。转折。那天早上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旨在把积极的情绪推入黑暗的深渊。
“就忽略它。就忽略它!”她有意识地告诉自己,但似乎一如既往,她的良心有自己的想法。
“你没有羞耻心吗?”那个声音斥责她。“你应该好好照照镜子。不只是看看你的倒影,而是……”它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好吧,我想,无论如何,这一切都在你的倒影里,但真的,你有没有停下来想过你的父母会怎么说?你死定了,玛丽莎!”它突然咯咯地笑了起来,那一秒钟,她的心似乎都停止了跳动。她的身体静止了,甚至停止了走路。她的思绪现在变得混乱了,她沉浸在记忆和对他们反应的预测中。
直到现在,她骨子里的逃避主义者都不允许她去想这些事情。她甚至设法把她的记忆,她的良心放在一边。那个小恶魔总是很有效,知道要按什么按钮来让她更加疯狂。
一击之下,它摧毁了她所有的城墙,打乱了她的顾虑,她终于屈服于恐慌。一种从那天早上一切开始就一直困扰着她的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