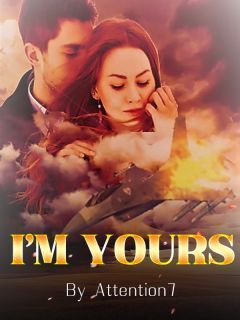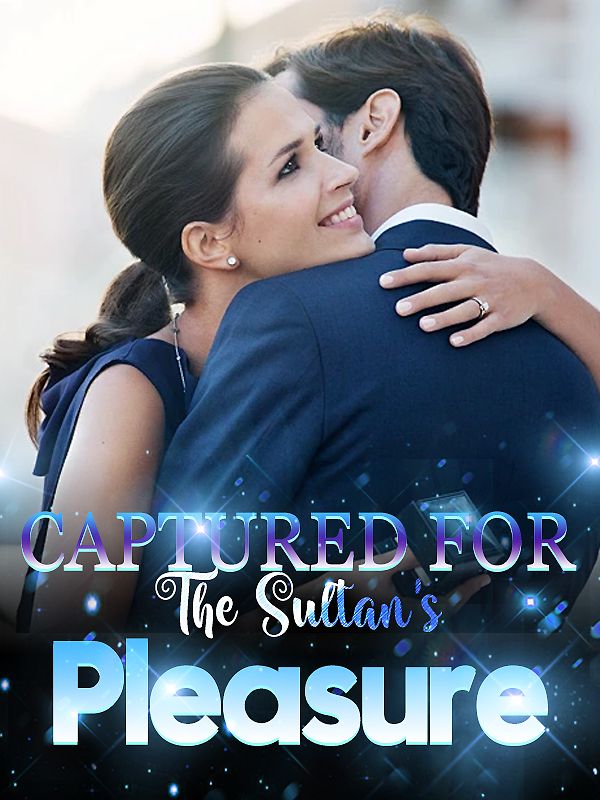瑪麗莎氣炸了,眼前一片紅。今天原本開局不錯,結果卻成了她人生中最衰的一天。
她等了超久。久到她都快放棄自己了。她甚至想過要改名換姓。一個全新的名字,把她過去的黑歷史全部抹掉。
今天本來是個超棒的機會,可以讓她重新踏入社交圈。但,經歷了早上發生的那些事,除非奇蹟出現,否則她就完蛋了。
所以,對,她很火大。
四年來的努力全泡湯了,她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更氣自己,還是更氣那個混蛋,竟然惹出這種事。
他幹嘛老是把事情搞這麼難?如果他不在場,如果是別人,瑪麗莎肯定情況會好很多,至少不會像現在這麼慘。
他為什麼總是喜歡看她出糗?她想不通,但肯定是他的錯。她終於下了決定。
「啊!」她氣得扯著頭髮,怒吼。
「哪個白癡會跑去騎馬,而且還是大清早?」她對著自己咕噥,走在空蕩蕩的瀝青公路旁邊的小路上。
今天天氣超好,風景也很美。換作是平常,她肯定會停下來欣賞一下。沉浸在大自然的恩賜裡,但現在,同樣的景色卻像是在嘲笑她。那些景色在她心裡掀起了波瀾,讓她本就煩躁的心情雪上加霜。
但,白楊樹還是繼續在風中搖曳。棕櫚樹莊嚴地站著,對著中午的太陽揮舞著它們的枝幹。遠處,一座大城市的剪影閃爍著光芒。高聳、閃亮的玻璃覆蓋的摩天大樓,隱沒在一片綠色之中。
那原本是她的目的地。
她對這個念頭嗤之以鼻,但她的行為並不能抹滅这一切的美好。既不是城市,也不是它西邊幾里地之外閃閃發光的藍色湖泊。
那是烏爾布湖,是這座城市的瑰寶,也是維特魯姆的首都。她本來應該在那裡的附屬建築物裡,但多虧了他和他無休止的惡作劇,最終她沒能去參加她的新工作面試。
她的思緒飄回到那件事上,瑪麗莎發現自己對著她腦海中的回憶皺眉。
「他們是誰?」她自言自語,想著那些圍繞著他和她的另一個宿敵珍妮芙·馬瑟斯的女士們。
「他的訪客還是他後宮的一份子?」她刻薄地補充道。她還記得那個人對她說的話有多麼惡毒,這讓她很生氣。
「勾引他?真是個荒謬的想法!」她嗤之以鼻。她非常憤怒,怒火中燒,很快就變成了一種受歡迎的轉移注意力的方式,很好地為她的徹底逃避主義服務。因為這就是她本來的樣子。瑪麗莎是一個無法忍受承擔責任或承受她的行為剛剛播下的惡果的人。
這比思考替代方案或即將在維特魯姆的八卦圈中掀起的風暴更容易。更容易。她決定了,開始走上憤怒的道路。
「勾引他?」她對自己重複著這些話。她反思著這些話,只是為了不讓她的思緒朝那個特定的方向發展。
「好像我會墮落到如此卑微的地步似的。他覺得一個人可以變得多麼絕望?」儘管如此,她的原則仍然很重要,而且,發現他竟然會這樣看待她,讓她非常惱火。
不僅受到他的話語的攻擊,還受到當天早上的心理圖像的攻擊,瑪麗莎搖了搖頭,但那些想法並未離開她的思緒。
這很痛苦,而且越是這樣想,她就越是發現自己因沮喪而呻吟。她很努力地不去扯自己的頭髮,而且從所有的精神入侵中都可以看出她的臉上充滿了挫敗感。然而,她仍然發現自己想知道,「我現在該怎麼辦?有沒有辦法挽救一個已經徹底毀掉的情況?」她思考著,同時低頭看著她那隻滿是泥濘的鞋子,這與她現在踩的乾淨的灰色柏油路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根本沒有其他辦法。她終於承認失敗。沒有辦法避免後果,而這次,這將是一場史詩般的醜聞,如果不是比四年前那場醜聞更大的話。
「我為什麼不能放過那該死的圍巾呢?」她咒罵著,她那隻穿著紅鞋的腳又踩到了一塊石頭上。鵝卵石鬆動了,散落在她前面的主要公路上。
「還有那該死的風!」她刻薄地說道,拖著一隻赤腳和一隻鞋跟壞掉的紅色鞋子,走在狹窄的柏油路上。
她本人的外表就證明了她的磨難,考慮到她那天早上那糟糕的心情。這也解釋了她每走一步都會不斷飛出的那些鬆散的石頭的數量。
她很幸運,這條路也空無一人。它通常是空的,但由於她早上不幸的轉變,她也懷疑大自然本身也在串通一氣,想讓她丟臉。
「大自然在陰謀對付你?」一個聲音嘲諷道。
她能聽到它裡面的笑聲,以及更多,她最不希望聽到的舌頭上的惡作劇。
「現在不行……」她在心裡呻吟道。「我今天已經夠難的了,不要再往裡面加這種瘋狂了」她對自己說道。
「或者,這是一個真實的人在說話?」她抬頭看了看四周,並敢於希望。
「是我,笨蛋!」那個聲音補充道,瑪麗莎簡直不敢相信自己倒楣。「你怎麼抓不住事情是如此令人驚訝。把你置於所有這些愚蠢之中,這有什麼意義呢?」這個聲音嘮叨著,她可憐的心再也受不了了。
驚喜。轉折。那天早上發生的所有事情似乎都旨在將積極的情緒推入黑暗的深淵。
「就忽略它。就忽略它!」她有意識地告訴自己,但似乎,就像往常一樣,她的良心有自己的想法。
「你羞恥嗎?」這個聲音斥責她。「你應該好好看看鏡子裡的自己。不僅僅是你的倒影,而且……」它停頓了一下,似乎在思考著事情。
「嗯,我想,無論如何,這都在你的倒影裡,但真的,你停下來想過你的父母會說什麼嗎?你死定了,瑪麗莎!」它突然咯咯地笑了起來,她的心似乎停頓了片刻。她停下了,甚至停止了走路。她的思緒現在一片混亂,甚至沉浸在一個又一個記憶和對他們反應的預測中。
到目前為止,她的逃避主義者一直不讓她思考這些事情。她甚至設法把她的記憶、她的良心放在一邊。這個小魔鬼總是能有效地知道要按哪個按鈕才能把她逼疯。
一擊之下,它摧毀了她所有的壁壘,並且打亂了她的抑制,因為她最終屈服於恐慌。一種從那天早上開始就一直困擾著她的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