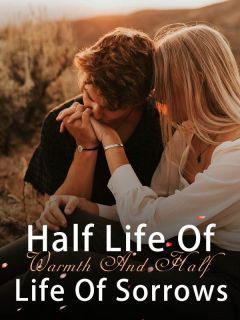艾莉亞娜
李奧納多·達文西曾經寫過,黑色就像一個破爛的容器,什麼都裝不了。 我很好奇他對白色的看法。 他覺得這是一種純潔的象徵嗎? 還是他也把白色看作是一種虛假的明亮,一個謊言?
兩年前,如果我站在這個講台上,對面站著這個男人,我會像現在這樣微笑。 那時候,白色的禮服緊緊地裹住我的身體,承諾著誠實和信任,因為我散發著溫暖,把我的胃緊緊地纏在一起。
只有那時,我的微笑才會感到舒服,充滿了真心的喜悅,因為那時我愛他。 在我生命的那個人生階段,他是我的世界,我會把自己鋪在他走過的地方,用他沾滿鮮血的鞋底走過。 我會赤身裸體地去做,準備好向這個男人敞開心扉,臉上帶著微笑。
一個不那麼大膽,也不充滿復仇低語的微笑。 我的心會跳動著愛,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潛伏在教堂牆外的威脅,等待著即將結束的有限耐心。 這場婚姻不是童話故事。
是的,整個場景曾經有潛力成為一個偉大的民間傳說故事的完美意象,魔鬼娶了他的天使。 但我不是天使,我是壞人。
既然我要坦誠,我也應該指出這個男人不是魔鬼。 魔鬼曾經是天使。 馬可 Catelli從未知道過什麼是純潔的感覺。
他只知道邪惡、傷害、痛苦和仇恨。 而且,這座教堂裡唯一的偉大之處,就是我對這個男人、我未來的丈夫的仇恨。
他抬起我的手,把它包在他的手裡。 我不需要看著人群,就知道女人們正用厭惡和嫉妒的眼神瞪著我。 我要嫁給一個Catelli。
很少有人對這次結合感到高興,而且他們可能認為Marco握著我的手意味著他愛我。 但我向你保證,愛並非如此。 他捏著我的手,他那玩世不恭的眼神正在一遍又一遍地刺穿我。
馬可 Catelli正在向我展示他很快就會控制我。
這不是愛的結合; 這是死亡的結合。 Marco娶我,不是為了他聲稱未來要和我一起創造的生命。 他娶我,是為了報復他已經佔有的那個人。 他把這枚戒指戴在我的手指上,因為我才是他現在需要的工具,用來組建他的軍火庫,開始一場戰爭。
我是最後的選擇。 他走向黑暗的最後一步。 而我不可避免的提早下葬,是他唯一的慰藉。
我的父親告訴我,Marco對我著了迷。 但我知道那不是真的,馬可 Catelli唯一的痴迷是沉迷於權力。 它蒙蔽了他,以至於他看不到,我,Alianna Capello他未來的妻子,是他最危險的敵人。
如果他認為我會任由他利用我,當他意識到我不是他如此愛慕的那個小老鼠時,我會享受他的痛苦。 Camilla Moretti很愚蠢,而導致她過早死亡的任何事情都是她自己造成的。
她想和錯誤的玩家玩遊戲,像Ren一樣; 他們像一枚棋子一樣把她幹掉了:- 毫無價值,可以丟棄。
但對我來說,我已經獲得了女王的地位。 我和Marco最大的對手Lucca Sanati一樣邪惡和狡猾。 他們都在尋找的那個人。 一個選擇把我變成敵人的人,當他碰了他不應該碰的人時。
「你是否願意娶Marco Catelli為你合法的丈夫,無論疾病還是健康,直到你們都活著?」 不字來到了我的嘴邊。 我應該這樣說。
我的真愛仍然埋葬在淺淺的墳墓裡,那裡仍然潮濕,就在這個男人的手中。 我應該說不。 我看著他,他剃得很乾淨的下巴,比我記得的更堅硬。 那些曾經燃燒著如此多熱度的黑曜石般的眼睛,我感到被陽光觸摸,現在卻空洞無物,讓我感到我的皮膚仍然覆蓋著雞皮疙瘩,從我到達這裡的那一刻起,37分鐘前。
「是的,」我說了,就像時鐘的滴答聲一樣,我虛假的微笑消失了。
我真不明白,一個簡單的詞怎麼會對一個人的生活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 這就是我現在存在的意義嗎? 這就是我的自由的全部意義嗎? 一個字,一切都消失了。 以卑微的自尊賣給了擁有最大頭銜的男人。 一切變得多麼膚淺? 我已經說了是,一切都已塵埃落定,現在我是Catelli夫人。
我深吸一口氣,昨晚的閃光讓我回憶起我來這裡的原因,我告訴自己,等待是我的唯一選擇。
我父親選擇的戒指被我的小堂弟Bernardino拿來,當我拿起它時,我的眼睛飄向坐在教堂前排的男人,我的父親,我的獄卒,他剛剛把我送走。
喉嚨深處一聲清了清嗓子,我的心跳動著,既害怕又緊張,因為我面對著我即將成為的丈夫,握著幾個小時前留在我的脖子上的手印。 有趣,不是嗎? 最好笑的是,我把戒指套在他的手指上,完全知道他還沒有對我做完。
令人悲傷的是,一顆淚珠出賣了我,它順著我的臉頰滑落。 生活有時會是一個殘酷的玩笑。
這一切是怎麼變成這樣的? 我什麼時候做了錯誤的選擇?
我叫Alianna Capello,Consigliere Sartini Capello的女兒,今天,2014年6月23日,我成了Marco Catelli的妻子,第五州的Capo Dei Capi。
殺了我的愛人、最好的朋友,現在還想殺了我的人。 這是我的自白。
-----
Camilla
6歲
美國,夢想成真的地方,白色的柵欄是必須的。
「Moretti小姐,你的祖父表示歉意,但他不會來參加你的生日派對。 他說讓你享受這個晚上。」
「他自己不能打電話告訴我嗎?」 我對Ridwano說,我的第二保鏢,還是第一個?
「Scusi 小姐。」 對不起,小姐。
我嘆了口氣,但沒有再說什麼,因為車子繼續沿著沒有真正目的地的道路行駛。
擁有Dante Moretti孫女的頭銜有利有弊。
好處很少,因為壞處總是打在我的臉上。 今天也沒有什麼不同,只是今天我沒有浪費這個機會,而是擁抱它。
「你能把我放在酒店嗎?」
司機沒有問我,我沒有把臉從華盛頓特區的街燈和熙熙攘攘的汽車上移開。 我今天23歲。 又一年增加了我對祖父的仇恨,又一年增加了我對父母和哥哥的思念。
我們在晚上8點之前到達酒店,在某種程度上,我很高興也很欣慰能進去。 從賓利車裡滑出來,如果你祖父是黑社會的教父,這是一輛標準的車,我衝到門口。
「Moretti小姐,你回來得真早,你晚餐吃得開心嗎?」 門衛問我,他打開門帶我進去。 他是一個矮胖的男人,大約50歲。 他讓我想起了去年9月我在阿拉斯加旅行時遇到的一個人。
「我很開心,謝謝你。 你這裡有酒吧嗎?」 我的長裙不是完美的酒吧裝扮,但絕對是我的風格。 黑手黨公主
「當然,這邊請。」 我走向他引導我的門,在我進入這個舒適的地方之前,我看到了昏暗的燈光和鏡子的光束。
「謝謝。」 我向離我最近的保鏢示意,要他給那傢伙小費。
這個地方有一種香草味,我進去時聞到了,然後朝酒吧走去,在那裡我坐了下來。 酒保是一個英俊魁梧的男人,大概30多歲。
「我能為這位女士點什麼嗎?」
「3指威士忌,任何黑色的都可以,16歲或以上。」
「馬上就來。」 酒吧周圍的架子設計成金字塔形的櫻桃木飾面。 數百瓶酒堆放在各處,迎合了各種各樣的顧客。
「給她一杯詹姆森·雅各。」 低沉的聲音來自酒吧的另一端,我的眼睛向那個現在吸引了我的男人移去。
「你是經理還是什麼?」 我很好奇。
「還是什麼。」 他藏在陰影裡,很難看清他的臉,但他的聲音很低沉,很乾。
我從椅子上下來,走向他,我的保鏢開始靠近。 我用手指給他們一個信號,讓他們放鬆。 我不想讓他們毀掉一個晚上,即使它還沒有開始。 我走近那個男人,然後我看到了製服。
「你是個士兵? 哇,我沒想到會這樣。 我從未見過美國士兵。」
他什麼也沒說,但當我坐在他旁邊微笑時,他用陰沉的眼睛盯著我。
「是什麼把你這樣的英國女人帶到這個好地方,穿成這樣?」
「今天是我的生日,所以我認為我會打扮一下,離開我的城堡,和一個英俊的男人喝一杯。 而且,這對你來說也沒有什麼區別,但實際上我是義大利人。」 他的臉刮得很乾淨。 他的頭髮剪得很短,頭皮上可以看到一個紋身,但在這個特定的區域,昏暗的燈光使他看起來像一個生動的夢。
酒保把我的酒拿到了這邊,當我喝了一大口時,我的眼睛染上了他英俊的臉,充滿了慾望。
「酒吧裡兩個義大利人。 有什麼機會。 就像你在看什麼?」 他問我,一陣笑聲從我的喉嚨後面冒出來。
「我還在看,等我看完再告訴你。」
「你並不像是普通的義大利人,你聽起來像英國人,你在這裡度假嗎?」
「是頭髮。 我把它染成了紅色。 是也不是。 我來這裡看望一些家人。 我想給我的表弟一個驚喜,他會很高興看到我,但我錯過了。 看起來他去了倫敦,打算給我一個驚喜。 是的,我喜歡我看到的。」
「夜晚還長,誰知道會發生什麼。」 當他說那句話時,我的整個身體都因為他並不微妙的暗示而變熱。 我從未當過暴露狂,但今晚盯著這個男人,我知道他即將改變這一點。
「如果我為了你錯過我的飛機,我應該得到一個名字。」
「你先說。」
「馬可。」
一個人朝我們走來,手裡拿著一個托盤,上面放著一部手機,打斷了我們的談話。
「先生,你的哥哥在打電話。」
他的眼睛盯著我,一絲認識把我對慾望的感覺轉變成更深層的東西。 難道是嗎?
「告訴我哥哥出了點事。」
「是的,先生。」
我笑了,一陣緊張感湧遍我的全身,因為我從小到大就愛著的那個男孩,坐在我的對面,渴望,而且根本不認識我。
「我能得到那個名字嗎?」
「這取決於你有多麼想要它。」